英特尔澄清内部代工模式,称各部门将自负盈亏
上周,英特尔举办一场投资者网络研讨会,深入了解释了该公司IDM 2.0芯片代工模式、以及英特尔代工服务(IFS)将如何融入这套模式。会上发布的核心信息是,英特尔已经将其技术开发(TD)、代工制造和IFS部门组合起来,并要求该部门自负盈亏。这一举措与英特尔此前技术开发和制造部门的工作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芯片巨头是将100%的运营成本分配给四个业务部门(BU),分别为:代工服务、客户计算部门(CCG)、数据中心与人工智能(DCAI)和网络与边缘部门(NEX)。在之前的业务模式下,各业务部门对自身行为缺乏成本敏感度。他们可以加快订单执行速度,并可随意重新调整设计,不会过多顾虑由此引发的财务负担。新的IDM 2.0模式要求各业务部门直接对其制造决策的成本负责,这种关系更接近第三方代工厂与不具备晶圆制造能力的半导体厂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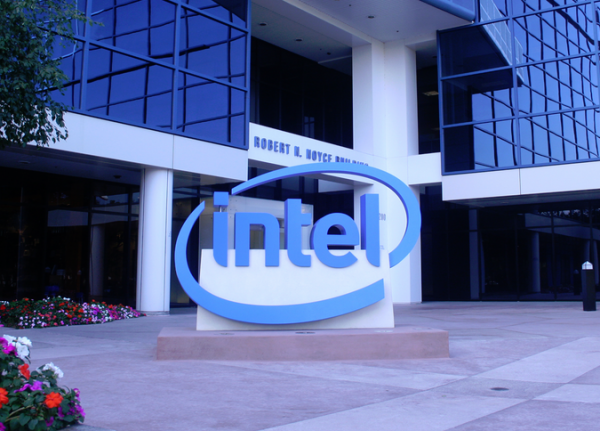
英特尔CEO Pat Gelsinger此举,是为了让部门中的每位成员对自己的行为更加负责。英特尔执行副总裁兼CFO David Zinsner表示,这项变动对于英特尔未来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凭借一系列改革,英特尔有信心在2023年内将制造成本削减30亿美元,到2025年改革结束时实现80亿至100亿美元的制造成本节约。Zinsner还提到,英特尔今年之内30亿美元的削减目标问题不大,其中包括20亿美元运营支出削减,以及10亿美元销售成本压缩。关于此次改革的更多细节,将随英特尔公司7月发布的第二季度收益报告一同公开。
由于技术开发和制造部门将向业务部门收取服务费用,因此英特尔正在采取类似半导体代工厂与外包半导体组装及测试(OAST)供应商间的行业执行基准,为包括IFS在内的四大业务部门制定标准化定价策略。这意味着英特尔的技术开发和制造部门将与外部厂商处于更加平等的地位。理论上,如果业务部门认为外部供应商提供的条件更优,则可以在英特尔之外寻求其他代工和OSAT服务。这些安排也符合Gelsinger希望英特尔恢复往日优势地位的愿景。Zinsner简要阐述了英特尔过往的问题:
“具体来讲,我们的制造、技术开发和IFS团队约占公司员工总数的40%、运营支出的25%和资本支出的90%以上。但是,我们对成果有效性开展基准测试,以及跟踪分配成本模型的能力一直有所欠缺且不够透明,难以确定投资究竟被花在了哪里。我们的重点是为制造业建立自己的损益表,这也是实现成本削减的重要前提。新的运营模式将增加业务透明度与可比较性,更直接地将我们团队与同行间的财务绩效做出对比,进而提示部门的真实经济状况。在加强决策和成本间关联性的同时,此番改革也将推动问责制的实践落地。”
英特尔副总裁兼集团规模部门总经理Jason Grebe也参加了本次电话会议,并具体介绍了推动这些变化的一大重要因素: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意识到无论是在工程方面还是早期开发方面,抑或是批量制造方面,我们都在工厂中投入了过量人力,希望加急送入物料并加快制造流程。但这最终反而降低了工厂效率,延缓了我们整体完整工具集的实现。因此,我们希望从流程、问责制和可追溯性等角度着手,立即解决这个问题。”
英特尔还为各业务部门制定了财务激励措施,强调以更积极的物料加急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保证业务部门有能力快速处理确需加急的订单。此举旨在尽量减少加急情形,甚至尽可能在晶圆帮层面消除这类状况。另外,新政策还会跟踪服务的加急请求和相应计费,让制造团队与英特尔的业务部门之间建立起更为合理的客户/供应商关系。
尽管这波变革将显著影响英特尔旗下各业务部门的固有习惯,但通过将制造决策的成本直接归入其责任范畴,新政将有望帮助制造部门降低成本并保持更强的行业竞争力。当然这一切还只是估计,未来实际影响仍然有待观察。另外,新政可能会影响技术开发部门在开发新工艺节点时的思路,而英特尔在工艺节点上已经处于落后。Zinsner专门对此做出了澄清:
“……因为我们会一视同仁,单纯考虑内外部代工厂的损益指标,因此制造部门将有充足的动力提升自身盈利能力,积极增加收入以维持自己的代工设施能够持续运转。他们将不遗余力地为此奋斗。”
事实的确如此。如果英特尔的代工制造业务不能着力关注运营成本和运营效率,将无法与外部半导体代工厂开展竞争,部门的损益表现将受到影响。而如果英特尔的技术开发部门无法开发出能够满足或超过其他竞争对手的先进工艺节点和业务订单,其损益表现同样会受到影响。最后,如果IFS不积极为代工业务争取外部客户,其损益表现也将受到影响。
Gelsinger表示在Andy Grove精神的感召下,他希望把强烈的责任感重新带回英特尔。他目前所解决的,是Grove早已预见到可能在公司内出现的问题:“成功会滋生自满情绪,自满会导致失败。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下来。”
也许Gelsinger不像自己的前辈、同样曾任英特尔CEO的Grove那般偏执,但他似乎很清楚该如何站在Grove的立场上审视公司的命运。
好文章,需要你的鼓励
CES上杨元庆首谈AGI,碾压人类的叙事不会让AI更聪明
很多人担心被AI取代,陷入无意义感。按照杨元庆的思路,其实无论是模型的打造者,还是模型的使用者,都不该把AI放在人的对立面。
MIT递归语言模型:突破AI上下文限制的新方法
MIT研究团队提出递归语言模型(RLM),通过将长文本存储在外部编程环境中,让AI能够编写代码来探索和分解文本,并递归调用自身处理子任务。该方法成功处理了比传统模型大两个数量级的文本长度,在多项长文本任务上显著优于现有方法,同时保持了相当的成本效率,为AI处理超长文本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Gmail新增Gemini驱动AI功能,智能优先级和摘要来袭
谷歌宣布对Gmail进行重大升级,全面集成Gemini AI功能,将其转变为"个人主动式收件箱助手"。新功能包括AI收件箱视图,可按优先级自动分组邮件;"帮我快速了解"功能提供邮件活动摘要;扩展"帮我写邮件"工具至所有用户;支持复杂问题查询如"我的航班何时降落"。部分功能免费提供,高级功能需付费订阅。谷歌强调用户数据安全,邮件内容不会用于训练公共AI模型。
华为研究团队突破代码修复瓶颈,8B模型击败32B巨型对手!
华为研究团队推出SWE-Lego框架,通过混合数据集、改进监督学习和测试时扩展三大创新,让8B参数AI模型在代码自动修复任务上击败32B对手。该系统在SWE-bench Verified测试中达到42.2%成功率,加上扩展技术后提升至49.6%,证明了精巧方法设计胜过简单规模扩展的技术理念。
联想集团混合式AI实践获权威肯定,CES期间获评“全球科技引领企业”
CES上杨元庆首谈AGI,碾压人类的叙事不会让AI更聪明
CES 2026 | 重大更新:NVIDIA DGX Spark开启“云边端”模式
Gmail新增Gemini驱动AI功能,智能优先级和摘要来袭
研究发现商业AI模型可完整还原《哈利·波特》原著内容
Razer在2026年CES展会推出全息AI伴侣项目
CES 2026:英伟达新架构亮相,AMD发布新芯片,Razer推出AI奇异产品
通过舞蹈认识LimX Dynamics的人形机器人Oli
谷歌为Gmail搜索引入AI概览功能并推出实验性AI智能收件箱
DuRoBo Krono:搭载AI助手的智能手机尺寸电子阅读器
OpenAI推出ChatGPT Health医疗问答功能
Anthropic寻求3500亿美元估值融资100亿美元







